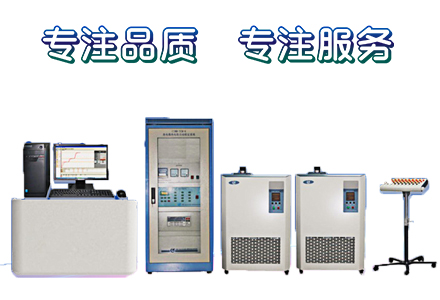生活中,有兩種人。一種人,得不到的東西是最好的,是胸口的朱砂痣,心底的白月光。另一種人,得到的東西才是最好的,弱水三千,取回的那一瓢才是真諦。
第一種人在乎的是精神上的審美,第二種人更在乎生活上的審美,究竟哪種更好?說(shuō)不清,于是就冒出個(gè)詞來(lái):中庸。就是在這兩種審美間尋找一種平衡——精神與物質(zhì)間的平衡,欲望與克制間的平衡。
只是中庸這東西,像端一碗盛滿的水,誰(shuí)都有端灑的時(shí)候。后來(lái)有的人聰明,為了不灑,干脆喝掉一小半。事實(shí)證明,那些活得比較滋潤(rùn)的人,都是喝了小半碗水的人,而不是那些緊繃著神經(jīng)的人。
和一個(gè)朋友吃飯。他問(wèn)我一些道路選擇上的問(wèn)題,我當(dāng)時(shí)心里充滿不確定性。我說(shuō),我不想我的一生,就如何如何過(guò)了。他笑了笑,突然像是哲人附體,說(shuō)了句:“你以為,一生很長(zhǎng)嗎?”這句話,卡住我好一陣子。我總在想,這是哪種審美?
精神上的?生活上的?好像都不是,又好像都是。我隱約從那句話里聽(tīng)出弦外之音:很多事,漫長(zhǎng)的彷徨中,抉擇中,遲早會(huì)得到一個(gè)答案。但是呢,那又怎么樣?等到答案來(lái)了,時(shí)間卻走了。答案,是個(gè)消耗性極強(qiáng)的東西。有時(shí)你為了求一個(gè)正確答案,消磨許多時(shí)間。最后可能一算,這答案還抵不上賠掉的時(shí)間。

站在一生的維度上,每個(gè)人的時(shí)間都是捉襟見(jiàn)肘。花有重開(kāi)日,人無(wú)再少年。一個(gè)人的韶華能有幾年呢?那被喝掉小半碗的中庸,就是不要答案。
你為什么喜歡這件事,為什么喜歡這個(gè)人,為什么要這么做?不要探討,不要分析,只需要表達(dá)出來(lái)就好了。或許有一天,你會(huì)明白,也或許你永遠(yuǎn)都不明白。但重要的是,你喜歡的事,已經(jīng)做了。
我畢業(yè)后不久,很多事情在心里盤成結(jié),無(wú)法紓解,最后做一趟漫長(zhǎng)的旅行——只揣著兩千塊錢就出發(fā)了,去哪里?不知道,到了車站再說(shuō)。看著蘇州這地名順眼,就去買蘇州的票。等到了蘇州,再想下一站去哪兒。就這么漫無(wú)目的地走,看未知的風(fēng)景,見(jiàn)從未見(jiàn)過(guò)的朋友。
回來(lái)后,很多事還是不明白,只是已經(jīng)不想明白了。人有時(shí)候僅僅是需要一個(gè)尋找答案的姿態(tài),其實(shí)答案到底是什么,并沒(méi)那么重要。答案或許是荒誕的,但尋找答案的過(guò)程不是。大抵浮生若夢(mèng),姑且此處逍遙。
知乎上有人講過(guò)一個(gè)故事:我嫂子在家做好了飯,等我哥哥回家。哥哥給嫂子打了個(gè)電話。嫂子接完電話,解開(kāi)圍裙要出門。我問(wèn)去干嗎?嫂子說(shuō),你哥哥給我打電話說(shuō),他回來(lái)的路上看夕陽(yáng),那夕陽(yáng)好看,叫我也去看看。
我喜歡這個(gè)故事,它融合了精神和生活的雙重審美。有煙火氣,也有詩(shī)意。
這世上嚴(yán)格來(lái)說(shuō),每個(gè)人都是“病人”:文藝是病,俗氣是病,嗜吃是病,貪財(cái)是病,癡愛(ài)是病,寡淡是病,小氣是病,刻薄是病,放浪形骸是病,碌碌無(wú)為還是病。有些人可愛(ài),就可愛(ài)在明知道自己有哪些臭毛病,但就是不肯悔改。
如果不妨礙到任何人,且能自得其樂(lè),這些病為什么要治?等你千辛萬(wàn)苦治好,時(shí)間已經(jīng)沒(méi)有了。你以為你的一生很長(zhǎng)嗎?不如做些喜歡的事。
 普天同創(chuàng)(深圳)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于計(jì)量測(cè)試產(chǎn)品研究、開(kāi)發(fā)、生產(chǎn)及銷售...
普天同創(chuàng)(深圳)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于計(jì)量測(cè)試產(chǎn)品研究、開(kāi)發(fā)、生產(chǎn)及銷售... 普天同創(chuàng)(深圳)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于計(jì)量測(cè)試產(chǎn)品研究、開(kāi)發(fā)、生產(chǎn)及銷售...
普天同創(chuàng)(深圳)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于計(jì)量測(cè)試產(chǎn)品研究、開(kāi)發(fā)、生產(chǎn)及銷售... 普天同創(chuàng)(深圳)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于計(jì)量測(cè)試產(chǎn)品研究、開(kāi)發(fā)、生產(chǎn)及銷售...
普天同創(chuàng)(深圳)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于計(jì)量測(cè)試產(chǎn)品研究、開(kāi)發(fā)、生產(chǎn)及銷售... 普天同創(chuàng)(深圳)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于計(jì)量測(cè)試產(chǎn)品研究、開(kāi)發(fā)、生產(chǎn)及銷售...
普天同創(chuàng)(深圳)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于計(jì)量測(cè)試產(chǎn)品研究、開(kāi)發(fā)、生產(chǎn)及銷售... 普天同創(chuàng)(深圳)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于計(jì)量測(cè)試產(chǎn)品研究、開(kāi)發(fā)、生產(chǎn)及銷售...
普天同創(chuàng)(深圳)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于計(jì)量測(cè)試產(chǎn)品研究、開(kāi)發(fā)、生產(chǎn)及銷售...